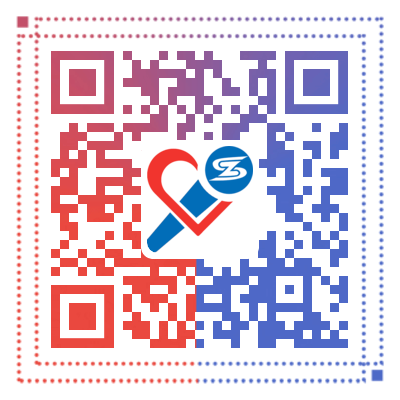中视小记者讯(贾文栋 贾志强)2018年11月,神山贾氏宗祠理事会成员聚在一起开会。会后,族叔贾新瑞老人与我交谈,说,神山这么大一个村子,竟然连一部村史也没有。他激励我挑头修史。我一时兴起,不知天高地厚,满口答应。在这之前,或许是父亲的去世让我懂得珍惜;或许是真的老了格外怀旧,我对故乡这块热土,开始留心探究,也在 《原平故事公众号》平台连续发表了多篇《神山风云》系列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被誉为“神山文化的挖掘者”。为了创作这些作品,我多次往返于城区和村子之间,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进行,对故乡的认识越来越清,对故乡的感情也越来越浓。渐渐地, 我被故乡的人文山水所感动,心中涌起一股久久不愿散去的家国情怀,也对父亲当年为什么要五修《神山贾氏族谱》有了更深的理解。

神山村史编委会会议中
鉴于此,一开始我是满怀信心的。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我才明白:要想做 成一件事,是多么地不易! 听说我要编纂村史,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支持者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积德行善的好事,其意义不可估量。反对者则众口不一。有人劝我,不要自不量力,那是要脱皮掉肉的,年龄大了身体要紧;有人劝我,故乡越来越没有人气,修史写给谁看?家里人除了担心我的身体外,还顾虑经费问题。 一旦书出来无人问津,印刷费谁来承担?一个靠工薪养家糊口的人,是不是有点管得太宽?面对各种意见,我首先想到的是诚信。咱既然应承下来,怎可轻言放弃?!当然,内心深处还有一点想法,那就是想证明给人看。父亲当年领头编修《神山贾氏族谱》五修本时,不过是一个初小水平都未达到的老农民,只有一腔热情。而今,自己好赖是大学毕业,总不会连父辈都不如吧?而一旦真正进入工作角色,我才明白, 自己确实是有点轻狂了、自大了。
一部村史,包罗万象,以一己之力,显然不能胜任。为此,我多次联络村里的有识之士,希望依靠众人的力量完成这件大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面临重重困难之际,总会有人与你风雨同行。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事迎刃而解。但修史过程中的孤独与无奈,唯有自己清楚。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调查清楚神山的历史, 我首先从搜集资料开始。除了回村找老人采访,去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我还依靠外甥女雪琴申办了 《神山故事公众号》,利用“大神山”微信群等网络,发布信息,收集资料。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陌生的面孔出现了,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提供资料,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也抓紧时间,一有空闲就回村调查,或钻进图书馆、档案馆,在书海中苦心寻觅。为了调查清楚一件事,我要采访许多人。
不到一年,我就采访村民近百人,如已经作古的贾升敖、聂文宝、贾西金、贾巨午、尚鸿儒、贾有庆、贾吉禄等前辈,还有健在的陈喜鱼(女)、贾丕礼、贾蒲明、贾白娥(女)、陈福田、 陈还忠、贾安仁、王亨祥、邢步龙、邢大立、贾福星、贾双前、贾金轩、白玉星等众乡亲,最大的接近百岁,小的也多过古稀。有的人见了一次不行,再见第二次、 第三次,有的甚至七八次,以至于个别人的子女,一看见我就嫌弃地说:“又来了!”而我除了手里的纸和笔, 一无所有,心里也感到过意不去。曾想过在 2020 年 春节的时候买点礼品看望一下这些老人,但由于疫情的到来,未能如愿。书尚未付梓,其中一些人,已是阴阳两隔,一别、永别了!还有一些计划中采访的人,如贾补田、贾召科、邢社会等,还没有来得及采访就去世 了!我还采访了神山女婿杨茂林先生,但因先生有病,见面时交流已很困难,以致他肚子里大量鲜活的资料无从探取。 除了回村采访,我还把原平图书馆“本地陈列室” 的书几乎一本不剩地翻了个遍,从中发现了大量珍贵的史料,也做了大量笔记。
但档案馆的查阅工作就不那么顺利了。因为调查的东西没有明目,工作人员无法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东西,而档案储藏室又不能随便出入,给查阅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而且,有限的资料又多数是手写体,字迹潦草,加上时间紧迫,许多资料只能拍照后再去整理。为了尽快拿到第一手资料,我发动家人、朋友与我一起抄写、打印。尽管前后抄写笔记几十万字,还是留下许多的遗憾。比如,当费尽 心血将解放初村里的耕地情况一笔笔算出来之后,才发现由于记录潦草和抄写者理解上的不一致,致使旱地和水地的比例与真实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经过前期的准备,一年后,即 2019 年 11 月 3 日, 50余位神山村人与前来助兴的嘉宾共同参加了在原平南城街道办事处召开的《神山村史》编写研讨会。 会上,我提出了《神山村史编写大纲》,初步设定了十个章节,内容涵盖了从明、清、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直至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几百年间的神山历史。 时任原平市政协主席高秀亭从百忙中抽身亲临会场, 对村史编写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说要在浩如烟海的史实中选择有价值,有意义,对后人有启迪的人和事来重点记述,挖掘神山精神,为神山人民点亮一盏灯。
原平地域文化专家、《原平故事》主编杨晋生先生也到会祝贺、指导,满怀激情地谈到自己“对神山的再认识”。他说,这是一件没有多少人愿意干的苦事、难事,任重道远,并对神山人的文化执着表示敬佩。接着他从关注乡村文化,站在抢救行将消逝的乡村文明和乡村记忆的高度,肯定了这件大事的意义所在,并 就开展编写工作的具体方法作了详细的指导。
族兄贾秀恒虽因要务在身,没有亲临会场,但打来了电话,表示将全力以赴,做村史编纂的坚强后盾。会上,大家就编写工作做了简单分工,决定各负其责,分头行动。 就在我们紧锣密鼓、按部就班,开始村史编纂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工作部署,许多工作一时陷入困顿之中。身为警察,我被封闭管理,行动失去自由。在封闭执勤的日子里, 我一边整理收集来的资料,一边静心思考, 并抓紧时间“充电,阅读了好多史书。通过思考,我一次次梳理神山历史的脉络,从中寻找我写作的力量源泉,并最终确定了新的编纂大纲。
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把握着一个原则,那就是真实。为此,我力求做到对每一件事都追本溯源、写之有据。比如对“义勇军神山营”的组建,我就采访了 多个不同的对象,并给远在武汉的张光汉前辈写信核实。尽管如此,毕竟岁月久远,许多记忆会有矛盾。 我一边琢磨采访笔记,一边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符合史实。一些实在难以厘清的事实,就将不同的指证一并留存,留待后人查考。如神山邢氏族人提供其祖上曾有人做过崞县县令,根据年代和查阅《崞县志》推断,不符合史实,给予否认;而陈氏族谱记载一名先人在清末做过代县县令,则表明存疑而不断然否认。
对一些敏感问题,如土改、四清和文革等,我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记录,遵循叙而不论的原则,不受当事人情绪的影响。同时,我注重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村史大纲和村史主线多次向贾宣生、刘拾理、贾高锁、王海元等老师请教,力求村史不仅成为神山历史的记录,更成为神山未来的明灯。
编纂的过程,也是我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除了向书本学习外,我格外注重向身边的人学习。比如刘拾理老师,集勤奋与严谨于一身。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喜欢用数据说话。”这种理性的科学修史态度, 被我当做了编纂村史的座右铭。而尚然老师“村史编纂决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世界观,也让我走出了狭隘的小村,开阔了大视野,使神山定位有了新高度。 通过人物志的编纂,神山前贤往圣、仁人志士的事迹,也在时时温暖感动着我,在潜移默化中,我的心灵一 次次得到净化,精神一次次得到升华,心胸变得更加 开阔。来自同仁之间的关爱,也让我感受到了亲情之外的亲情,我在爱与被爱中愉快地编写,也同时完成 了身心的一次次修行。
在编纂的后期,通过《神山故事》等平台,我收到了许多回忆录和文艺作品。有些内容根据需要已经 汇入正文,有些内容则独立成篇,对正文作了详细解读与补充。大多数的艺文,情真意切,有的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惜乎村史容量有限,不得不一次次忍痛割爱。村史是一本集家族记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为一体的回忆录,所以,个人回忆录应该成为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为了统治需要,可能会在史书中有选择地记忆,个人记忆也因种种顾虑有可能选择性记忆,但个人记忆毕竟少了一些桎梏,有其补充细节的作用。为此,我收集各种文章达几百篇,逐一整理存档,最终虽只选取了少部分,似乎作了无用 功,但在选取时收获的岂是一丁半点,不管是鸿篇巨著,还是凡人小事,都对我的整体构思发挥了作用。 另外,那些民俗方言,虽然不是神山特有,却也是神山的一部分,我一并作了收集整理。
陶醉在文字的海洋里,乐此不疲,忘记了昼 夜阅读、打印带来的颈肩疼痛。全书初稿,字数达 150多万,期间又几易其稿,工作量可想而知,但我乐在其中,甚至连走路、吃饭也在构思。 也有人质疑,历来有国史、方志和家谱之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脉络,何必再画蛇添足?
但如果仔细读过《神山贾氏族谱》等谱牒,就会发现, 其中似乎缺少了什么。通过《族谱》,人们只能看到家族的繁衍发展过程,而对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 境却较少涉及,这就使得《族谱》像无根之苗,即使有根,也无非是“大槐树”下。
故而,村史与族谱相比,更具有根祖文化的特性,反过来也必将促进谱牒文化的 研究。而且,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许多村庄处于 巨变甚至消亡之中,再不进行村史编纂,恐落遗憾。
鉴于此,编纂村史,也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若此史,可慰前人功德,可励后来奋进,则 意足矣。 一部村史,如愿以偿,终于面世了。对于其到底 价值几何,已不在我的考虑范围。
人的独立性,注定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留住历史,是我们对后人 的庄严承诺;畅想未来,是我们对明日的满心期待。神山的未来,必将今胜于昔,更加壮丽!更加辉煌! |